吴根友 汪日宣:现代儒家政治哲学三种理论形态合论—以《大同书》《仁学》《政道与治道》三本著作为例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23-1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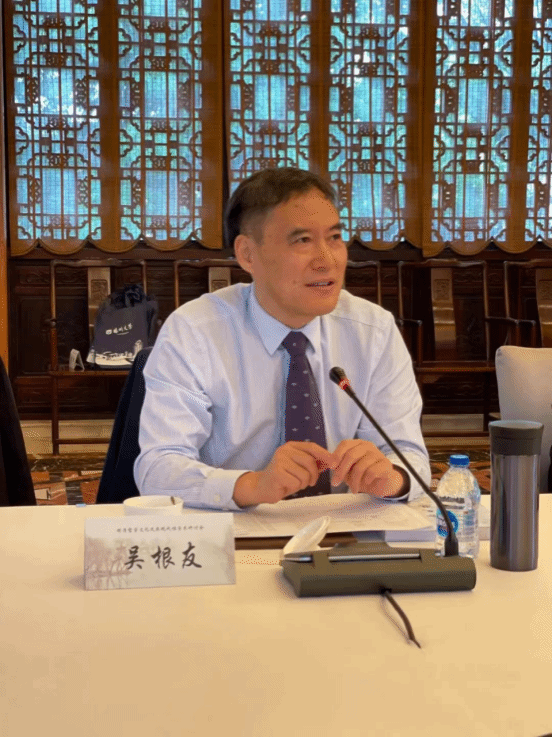
作者简介:吴根友,必赢中国官方网站教授,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国家级高层次人才;研究方向为明清哲学、先秦道家、中国政治哲学、比较哲学;汪日宣,必赢中国官方网站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政治哲学研究》第一辑(2023)
现代儒家可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算起,他们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现代西方的诸思想,活化传统儒家固有的思想创造出现代儒家的政治哲学理论。康有为的《大同书》以传统气本论为形上学,汲取现代西方平等、自由等观念,构建出康氏的新“大同”的政治哲学理论。谭嗣同则化用西方的“以太说”,在其《仁学》一书中构造出“仁通—以太—平等”的政治哲学理论,描绘出其“地球之治”的理想社会。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一书,在辩证考察中西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基础上,分析出两种不同的政治理性展开方式,提炼出“政道”与“治道”两个重要的政治哲学范畴,提出了儒家式民主的理想政治模式。现代儒家在古今中西的交汇点上,熔铸新旧,建构出既是中国的,也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哲学诸理论,这些思想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的再建构提供了可贵的思想启迪。
回溯近百年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从语言的角度上来看,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哲学”译名于20世纪初才进入中国,而作为正式学科的“政治哲学”的形成还要推迟到20世纪20年代。但是,具有现代意味的汉语政治哲学理论则在19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这百余年的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理论,既回应现代中国与世界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亦以理论的思维方式重建中国人的社会秩序观和世界秩序观,以理论自主与自信的方式参与当代社会的建设与当代世界的秩序建设。
本文选择三部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理论著作,即康有为的《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来考察现代儒家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的基本轮廓,进而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提供思想的前缘。
一、 康有为的《大同书》
鸟瞰现代汉语政治哲学发展的两条道路,并结合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学术史来看,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可谓中国政治哲学史书写的开端,而其师康有为的《大同书》则是中国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的先导。
如众所知,康有为发挥孔子的“春秋三世”说,融合现代西方进化论的思想,提出了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大同之世)。他自述其既生于乱世,又目睹人道凋敝,百姓疾苦的现状,覃思以救之,故而要构建“大同之道”,希冀以成“大同之世”。
众所周知,“大同”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最高理想,千百年来为无数儒家学人所向往。但真正对“大同”理想作出系统的理论阐发的,则康有为实为第一人。《大同书》是康有为政治理想之结晶,其在核心思想观念上以孔子思想为宗,以《礼记·记运》篇的“大同”理想为原型,以今文经学“春秋三世”为框架,以传统气本论为其政治哲学的形上基础,初步吸收了西方天赋人权、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进化论、柏拉图的乌托邦乃至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等诸多西方学说,构建出一个杂糅中西古今的康式“大同之道”,以之作为“大同世界”的社会政治建设方案。与宋明儒家“一体之仁式”大同理想社会相比,康式的“大同之道”包含现代资产阶级的平等、独立、自由诸新观念,这是康式“大同之道”超越中国传统固有政治哲学观念的地方,此点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作为一本充满理想性色彩的政治哲学著作,《大同书》的内容极其丰富,具有非常大的阐释空间。但就其基本的思想结构与核心内容而言,大体上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元气论或气本论为基础的大同之道。二是合乎“大同之道”要求的人类生活的基本原则是“去苦求乐”。三是结合中国化佛教与现代平等思想观念,提出了去一切界别的社会政治理想,大到民族国家,小到男女性别与个人之间的等级之界别。
康有为将“不忍之爱”看作人类群居相植的人道和文明的本质,而不是将个人的自由、人权看作人道和人类文明之本,这表明康氏“大同”理想的根本还是中国儒家的,是原始儒家与宋明新儒家思想在现代初期之延续与新发展。但他的“大同之道”与人道的根本原则在于“去苦求乐”。这又表明他与宋明新儒家提倡的克尽私欲、天理流行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仁爱思想,有了一些实质性区别,而具备了现代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一些思想要素,因而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气息。
他甚至认为,即便世上那些苦修不厌的人,也是以“求乐”为最终目的的。这一泛化的求乐论思想,与传统儒家的人生论与社会政治哲学颇不相同。“人道无求苦去乐者”,这可以说是康有为功利主义人性论与幸福观的经典命题,也是其“大同之道”的基本原则。按照人道“去苦求乐”的这一根本原则,康氏将“人道”分为三等:“立法创教,令人有乐而无苦,善之善者也,能令人乐多苦少,善而未尽善者也,令人苦多乐少,不善者也。”
因此,要想实现人类社会的进化,关键就在于如何让人类在世俗的现实生活中实现“去苦求乐”的最大化目标。《大同书》将追求人生的现世快乐作为大同世界里所有人的目标,而不是传统大同世界“一道而同风的良序社会”,也不是现代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与平等的“风俗画”(恩格斯语),应该说多多少少体现了康有为“大同之道”的理论特色。
要实现“去苦求乐”的人生目标,首先应知晓有哪些人世之苦。其次要了解致苦的原因。因此,“破除九界”的具体举措和方法,就构成了《大同书》的主体内容,而康氏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的核心精神和颇具现代特色的社会治理思想,亦得以充分地展现出来。
破国界为“破九界”之首。康氏认为,国家竞立,战争不止,为祸最烈,乃人类最大之痛苦。如何解决这一旷世难题呢?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康有为提出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他认为,今欲“去国靡兵”,实现人类政治大同,必须分三步走,逐步以三种政治体制实现人类的大同。
“破级界”是大同政治制度确立后,进一步讨论大同社会的制度和价值秩序的问题。康氏认为,大同世界以平等为第一价值,而人类社会之不平等莫过于“男女,人种,阶级”三大类,故必须破之去之。“阶级”的本义就意味着不平等,而“级界”之中,贱族、奴隶和妇女三种级界,最为不平等,也是最为惨烈的。“破级界”则必破除一切之不平等。
要而言之,“破除九界”,以成至仁、至公、至平的“大同之世”,是康有为实现大同理想的具体操作方法与实现的路径。其中包含很多空想的成分,但立意高远,想象力丰富,既具有理想主义的卓识,又富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是现代中国初期古典儒家士大夫在接触了现代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科学思想之后,以富有强烈民族情怀和人类主义的政治情怀,创作出的一本杰出的政治哲学著作。如果将其称为现代汉语政治哲学中的《理想国》,相信柏拉图不会起诉我们命名方面的侵权,而康有为也会微颔一笑。
二、 谭嗣同的《仁学》
谭嗣同,近代中国历史和思想史上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思想家。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他以身殉道,与梁启超诀别时说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去世后九十日,梁启超将其遗著《仁学》一书在自己主办的《清议报》上全文刊发,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仁学》,以宗教之魂,哲学之髓,发挥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与《大同书》欲建构儒家式的理想国目标在形式上稍有差异,谭嗣同的《仁学》一书则希望建立一个“仁—通”的理想社会。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仁学》“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这一“仁—通”的理想社会,按照其开篇“仁学界说”的二十七条内容来看,大体上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即“所以通之理、之具”、“通之象”、“通之方法”、“通之效”与“通之名”,即通之语言表达。从整体来看,《仁学》全书是以“仁—通”为核心理念而建构起来的“现代儒家”的理想国。这一理想国有其自己的形上学内容、具体表现形象和实现其理想的具体方法。其形上学所以通之理——仁,不必多说。而“所以通之具”——以太,则是谭嗣同从现代西方科学知识体系里借用的一个概念。此概念代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气”的概念,而让“仁之通”具有一种物质性的凭借,使得其“仁—通”的政治哲学观念具备了现代性气息。因此,将《仁学》看作中国现代儒家当中一部可与《大同书》相媲美的政治哲学的理论著作,并不为过。“以太”原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解释世界的五大物质元素之一,至17世纪起,西方近代物理学的兴起而转化为一个科学的概念,表示充满宇宙且渗透万物的物质,其特性是可以作为声、光、电、热、风、雨、霜、雪等形式能量的传导介质。“以太说”在19世纪极为兴盛,为谭氏所吸收后,改造为自己哲学的本体论概念。从体的方面看,“以太之体”是一种物质也是一种介质。它极广大而至精微,无所不在又无从感知,是宇宙万物得以形成的基础,也是宇宙万物在本质上相通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以太的本性就是恒动不已和永恒的自我更新。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和变化不已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以太恒动的本性。从用的方面看,体现在不同学说和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的“仁”之观念和行为,乃是“以太之用”,此种作为以太之用的“仁”以“通”为第一义。从“通之象”——平等和四通的角度看,《仁学》的政治论和社会论以平等为价值核心,以追求四通为具体目标,而以追求“地球之治,大同之道”为最终目标。其政治论的内容可分为政治批判论和政治理想论两大部分。而政治理想论包含社会论中以平等为核心价值的具体内容。谭氏的“政治批判论”主要针对“名教”,并主张以“平等”的精神改造旧伦理。谭氏主张“名为实宾”,认为“名”作为人造概念是对真实存在的思维反映,而非真正的实体,并且其内涵和价值也常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而变化。以名为教,实际上是对真实世界的虚假歪曲。谭氏揭露出专制统治者以名教(三纲五常)的意识形态制约人身更钳制人心,歪曲真正的伦理精神,使得人我之间始终横亘着无法逾越的鸿沟。于是,谭氏大力批评“名教”祸乱“仁通—平等”,希望破除“名教”以为新的道德伦理铺路。而欲破名教,必首破君民、君臣之间的政治纲维和道德伦理。至于父子之纲,谭氏以父子皆为天之子而大倡父子平等,又以仁为天地万物之源,而大倡天人平等。至于夫妻之纲,谭氏则举平等之精神痛批包办婚姻的荒谬和男女不平等的残酷。谭氏除了批判旧伦理的恶毒,同时也发掘了旧伦理中的宝贵精神。清末之时,谭氏是第一个敢于在思想学理上彻底批评名教(三纲五常)的思想家,其批判思想极具进步意义,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谭氏除了批判名教和君主专制政治之外,还重新审查了与名教相关的其他伦理道德。从“通之方法”的角度看,其“破对待”的最终目的是要将“通之象——平等”在现实社会政治中加以落实。往近处说,则首在变法自强,通商、通政等,往远处说则是要达成“仁之四通”的境界,即实现平等自由的“地球之治:大同之道”。因此,在这里,我们将“通之方法”与其政治理想论放在一起讨论。谭氏根据《易》之卦理作“逆三世”与“顺三世”之说以解决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的问题。所谓“逆三世”,即太平(元统,洪荒太古)—升平(天统,三皇五帝)—乱世(君统,三代)的历史发展过程。所谓“顺三世”即再由乱世(君统,由孔子以至于今)—升平(天统)—太平(元统)的未来发展过程。当历史循环上升发展到“顺三世”之“元统太平世”时,就达到了谭氏心中众生自由平等的“地球之治”:谭氏所勾勒的理想社会是一副完全自由、平等、均富、独立、和平、友好的大同世界。在这个理想的地球之治中,谭氏提出了颇具浪漫和幻想色彩的社会构想。欲实现“地球之治”,在物质基础方面,谭氏强调农业为本,通商两利,重视机械化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物质生活以及人类自身改善的积极作用,其中不乏合理性的要素。在社会政治和精神文化方面,“地球之治”的核心在于平等。欲实现“仁通—平等”,其总方法就在于“破对待”。概括地说,谭嗣同的《仁学》一书,紧紧抓住儒家哲学的核心价值“仁”的观念,在“通”的新观念里构建了“仁—通”的新政治理想,从而与康有为的“大同”政治理想并时而成为现代早期儒家政治哲学理论的两面旗帜。《仁学》一书在三教融通、中西融贯的基础上,通过“以太”作为“仁—通”的质料性之具,建立起以“仁通—以太—平等”为逻辑主干的现代儒家的政治哲学理论,古老的儒家“仁学”焕发现代的思想气息,并由此生发出具有现代性又有超现代性的“大同之世”或“地球之治”的社会政治理想。
三 、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
20世纪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理论的诸形态当中,现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理论内容亦十分丰富。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和张君劢等人,均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按照郭齐勇教授的概括,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整体特点是:
以现代民主政治为参照深入反省传统政治思想的不足与缺陷,认为民主政治是儒学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又以儒家整全的人文精神为背景,批评现代民主政治所包含的诸多弊病,并寻求克服之道。
为了叙事方便,我们在此处选择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一书为典型,考察现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理论。
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一书主要探讨了两个中心问题:“一为政道与治道之问题,而主要论点则在于政道如何转出。二为事功之问题,用古语言之,即为如何开出外王之问题。”为讨论并解决这两个中心问题,牟宗三建构了两个核心工作术语,即“理性之架构表现”和“理性之运用表现”。“理性之架构表现”术语对应的是“政道”概念,“理性之运用表现”术语对应的是“治道”概念。
就其理论背景来看,牟氏政治哲学有两重背景,一是中西政治哲学理论异同之比较的广阔文化背景,二是站在中国现代社会历史现实之上瞭望的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和理论的观念背景。
基于第一个背景,他将中西政治哲学理论中的文化元素从哲学上加以明确的区分,认定中国文化偏重在理性之内容表现与理性之运用表现上,而西方文化则偏重在理性之架构表现和理性之外延表现上。基于第二个背景,他将“理性之架构表现”看作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之实质。换句话说,只有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才有“政道”,而非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则“无政道”,而至多有“治道”。后一重背景,使得牟氏的政治哲学的“政道”与“治道”概念所应有的理论普遍性大大降低,同时也导致了他的政治哲学严重地贬低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高度,因而也无法很好地解释中国传统政治现象及其固有的思想资源。
就中西政治文化异同之比较方面而言,他认为,中国文化是“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之文化,其特点是“圆而神”;而西方文化则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之文化,其特点是“方以智”。两种不同精神特质的文化生命展开出不同的理性表现。因此,“理性之运用表现”和“理性之内容表现”是“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下的理性表现方式。因而构成传统中国政治哲学之特色。而“理性之架构表现”和“理性之外延表现”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下的理性表现方式。因而构成西方社会政治哲学之特色。而中国文化之所以没有发展出西方的民主政治和科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及其理性展开的方式。牟氏从中西文化的角度讨论中西政治制度的差异,有其深刻性的一面。
牟氏还试图分析中西理性展开方式差异的内在原因。他指出西方政治之所以发展出“理性之外延的表现”,其本质的因缘是他们形成智的文化系统之“概念心灵”,而现实的因缘则是他们历史现实中的“阶级斗争”。西方人在不断的阶级斗争中为阶级谋取公利,其中内含了争取正义、公道、人权与自由等理念,并通过基督宗教改革和自然法的天赋人权运动两个关节实现其理性之外延的塑造。反观中国,牟氏认为中国政治之所以发展出“理性之内容的表现”,其本质原因是中国文化系统之“实际的直觉心灵”,而现实原因在于中国以前的政治活动的事实只是那样自然的演变,人因才、德、能而有“位”而尽其“分”,没有阶级斗争,政治就实际生活一起全部敞开而承认之,政治就是生活。牟氏对中西政治理性展开方式的追问和回答具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但是也掩盖了或逃避了关键性的问题,一方面他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示了西方政治形成的文化思想特色和社会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又未能真切地把握中国政治历史的真实形态及其复杂性。
由于牟宗三是参照现代西方政治的现实与理论,来讨论“政道”与“治道”问题的,因此,他的政治哲学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政道与治道的理论探讨方面,而是以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现实与理论为参照系,探讨中国社会如何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开出现代的民主政治形式。因此,他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缺陷与不足,以及如何通过“曲通”的方式实现自我的创造性转化。
牟氏认为,“政道是一架子,即维持政权与产生治权之宪法轨道,故是一‘理性之体’;而治道则是一种运用,故是一‘智慧之明’。有政道之治道是治道之客观形态,无政道之治道是治道之主观形态,即圣君贤相之形态”。而中国的传统政治属于后者。在治道与政道相须相存的问题上,牟氏认为,中国以前的治道“已进至最高自觉境界,而政道则始终无进展”。更具体地说,中国传统的政治没有发展出政权、主权、自由、权利等形式概念(理性之架构的表现)。从“得天下”的角度来看,儒家政治思想中的“天与”“人与”等观念,又模糊了“公天下”的政治理想,让“家天下”变成合理的政治形式,而不能正视“家天下”在制度和道义上的不合理性。就“治天下”的角度看,一方面“仁者”可遇不可求,导致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后果,另一方面则又让“治者”的负担过重,使其被寄予过高的期望。
从学术的角度看,牟宗三将中国传统的“治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儒家德化的治道,二是道家的道化治道,三是法家物化的治道。因此,如何让中国文化转出“政道”,就成为牟宗三接下来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最终落在了“政治理性”的部分。
关于政治理性的探讨,是《政道与治道》的主体内容。他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治道至极而无政道”,“中国文化如何转出政道”是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化的一大关键。解决这一问题,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和前进的方向,也是新儒家的历史责任。对此,牟总三提出运用“理性之架构”的现代民主政治方式来改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张。他说:“政道之转出,事功之开济,科学知识之成立,皆源于理性之架构表现与外延表现。”
《政道与治道》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政治哲学著作,远非本文所能涵盖。从学术的角度看,该书的第三和第四部分在讨论政治的基础问题时,涉及了政治神话、政治科学以及政治与道德等诸多问题。在“政治神话”的问题上,他将法国学者都特关于政治神话“是人格化的集体欲望”的说法,修改成政治神话是“人格化的集体愿望”的表达式,进而解释某些政治运动中一些表达了“公共、客观的集体愿望”,为何能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和创造力的原因。他还由“政治神话”的问题衍生出古代英雄主义和近代集体主义的政治形态问题,并由此出发集中但不正确地批评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不过,他基于“政治理性”的基本观念而对各种政治神话的命运作出了自己的预言,则颇有见地。
在“政权与政道”和“治权与治道”的关系上,牟氏既理论化地说明了政权依据政道、治权依于治道的一般性原则,也以之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来解释中国传统政治之缺陷,以及其为何不能发展出现代的民主政治之原因。牟宗三虽然高扬“理性之架构”的作用与意义,推崇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但作为现代新儒家,他继承了儒家的仁爱思想特别是宋明诸儒学发展起来的“一体之仁”的思想,又吸收了近代以来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依托儒家思想所发展出的世界主义的政治理想,因此,其对现代民主政治对内造成虚无现象、对外造成野蛮现象的双重弊病,还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认为,西方社会历史由于阶级斗争、宗教、自然法与天赋人权而建立起诸如法律、契约、权利等外在的形式的理性的概念架构和纲维之力,成就了民主政体,恢复了政治自性。但这种外在的形式的纲维之力,使得个人主观生命难以顺势调畅,使得整个世界“一方面外在地极端技巧与文明,一方面内在地又极端虚无与野蛮”,遮蔽了政治世界的可靠基础。这一批评,虽然未能触及建立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的实质性弊病,但毕竟没有完全陷入对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盲目崇拜之中,而挺立了中华文化的自主性,表现了中华文明在身陷历史艰难之际而仍然能保持一种对外来文化的鉴别力与取舍能力,从而能展示出文化的自信。这是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的牟宗三所具有的可贵的精神品质。而他从古今中西一般的政治现象出发,析出“政道”与“治道”两个概念,以之分析人类政治理性的两种不同表现形态,对于现当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建设,特别是对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理论建设而言,无疑是贡献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理论遗产。
四、结 语
相对于龚自珍、魏源及他们以前的儒家思想家而言,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应当属于现代儒家。由于现代学术界使用的“现代新儒家”概念有特定的内涵,故本文暂使用现代儒家的概念囊括自康有为以来的现代所有儒家思想者,现代新儒家只是现代儒家的一个子集。本文不是全面地讨论一个思想家的政治哲学思想,而是着重从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这一特殊视角来考察现代儒家政治哲学理论的代表作,以展现他们的政治哲学的理论形态,同时也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侧面地回应了中国有没有哲学的大问题。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宏大的事业,而理论形态的建构是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一个核心工作。如何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新形态,回顾近百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固有的理论遗产,显然是一项基础性且十分重要的学术史清理工作。本文在此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后面还会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
